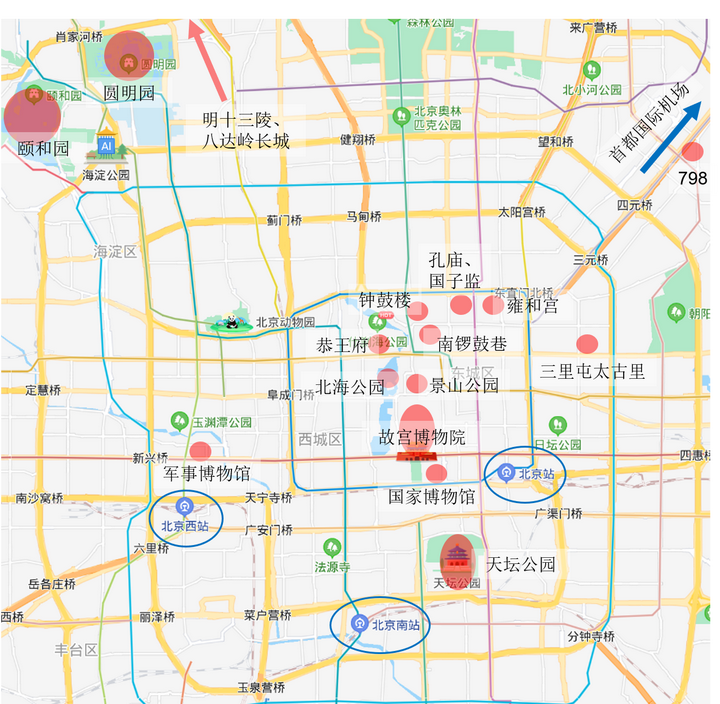花桥|史读桂林 十年心事一灯前
2025-04-03 12:29:00 实时讯息
之前我们聊到了蔡戡,这个蔡襄的后代,十三世纪初来到桂林当广西老大,当了最多一年时间,就辞职不干了。然后,接班的是福建人詹体仁。
前面我们说过,纵观历史,但凡世纪之交的时候,总是会有些大事发生,南宋的这段世纪之交,影响力最大的事情,莫过于庆元党禁了。来桂林接班的詹体仁就曾深受其害,庆元初年被列入五十九人的伪党大名单,罢官后,在家里无所事事虚度了八年光阴。对于一个已经年过半百且还有仕途追求的人来说,这八年的虚耗,前途不说尽毁,再出山时起码也已经是日落西山的感觉了。
有人说,桂林地处偏远,庆元党禁发生在朝廷中枢机构,对桂林影响有限,怎么可能呢?就像往池塘中央扔一块石头,哪怕池塘再大,初兴的波澜漫到岸边时已经弱化成了涟漪,那岸边的草木还不是要无助地晃荡好久?以文人为主力的南宋官场,在庆元党禁运动中受波及的自然文人居多,而受波及又在桂林任过职的至少有五人,受负面影响的有詹体仁和吴猎,而短暂受益的有三人,比如我们聊过的张贵谟——蔡戡的前任——另两位则是更早一些的应孟明和陈贾,他们都曾坐在过张贵谟同样的位置上。

中华书局出版的《南宋制抚年表》一书里清楚地记载了詹体仁远离朝堂的年头。
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
庆元党禁的这份五十九人伪党大名单,后人也曾质疑其准确性,比如说宰相周必大进了名单,但著名诗人杨万里因为党禁的原因罢官,却没有列入其中,就让很多人不解,这也太看不起人了吧?而薛叔似、皇甫斌一度荣列其中,但韩侂胄失败后,两人又被列入了敌对的韩党圈子,中间有何变故,也是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不过,至少可以确定的是,詹体仁进了这份名单,张贵谟则在另一份攻击“伪党人”的名单中,同在后一份名单上的还有1189年接应孟明班当上广西老大的陈贾(之前我们曾用很大的篇幅聊过陈贾),与应孟明不置可否、最后不参与的态度不同,陈贾是韩侂胄手下的急先锋,时任兵部侍郎。
张贵谟嘉泰二年(1202年)离任,詹体仁嘉泰四年上任,中间只隔了个任职一年的蔡戡,而蔡戡虽没入伪党名单,但又和当时的运判吴猎关系不错,曾一同出游,还在桂林的隐山上留了石刻。本属两个阵营的主官在这十余年时间里陆续执政一地,还能说桂林的官场生态丝毫没有受到庆元党禁的影响?
无论如何,这都是元祐党籍之后,南宋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又一场浩劫,后人评价说,随着打击面的扩大,这次运动的后果,是乾道、淳熙年间那种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而不复返。想想也是,但凡和这些人有关系的,都或深或浅地遭到了牵连,不能当官,甚至连科考都不能参加,硬生生地掐断了上升通道啊,谁还敢多说话,乱说话。而投向韩侂胄阵营的陈贾以及张贵谟,在韩侂胄倒台被杀后,日子又能好过到哪去?拥有大智慧的应孟明倒是得了个善终,一直在朝廷干到了七十九岁。
其实,前面我们在讲到朱晞颜(1194—1195年帅桂,1195年是庆元元年,正是庆元党禁的开始)的时候,曾经聊过庆元党禁的话题,这里就不再重复太多了,大概就是赵汝愚和韩侂胄两派之争,然后很多人被卷了进去。
赵汝愚是皇室宗亲,韩侂胄是外戚,在绍熙五年(1194年)的“绍熙内禅”事件中,以赵汝愚为首、韩侂胄为辅联手宗室成员赵彦逾发动了一起宫廷政变,扶赵扩上位,也就是宋宁宗时代。尘埃落定后,赵汝愚独掌大权,志得意满,却忘了让韩侂胄当节度使的承诺,从此点燃了两人之争的导火索。
赵汝愚也不是啥都不懂的俗人,他把有大师之称的朱熹拉到了自己手下,还安排他当了皇帝的老师,试图以朱熹在文化人圈子里的影响力来巩固自己的地盘。但他还是大意了,低估了韩侂胄这个“南宋第一外戚”的能量和智力,终究是被韩侂胄掀翻,并身死他乡。而掀翻赵汝愚,韩侂胄就是从朱熹这个赵派最大的旗手开始,一步步布局的。
现在我们知道,詹体仁恰好是朱熹的学生。事实上,在绍熙内禅一事中,詹体仁也是参与者之一,所以,他是直接就上了黑名单的。这么说起来我们就明白了,刚开始的时候,詹体仁和赵汝愚、韩侂胄都是一伙的,而且还属于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圈子,后来分边后,朱熹才加了进来。然后赵汝愚败了,身死道消,朱熹和詹体仁都受了牵连。
韩侂胄称赵汝愚、朱熹们为伪学奸党,他自己后来却也被文人称作奸臣、权臣,而且还是被另一奸臣所害。真是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兜兜转转一圈下来,这南宋,原来都是奸党啊?有些时候,文人对历史的描述,就是这么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是如你所知,韩侂胄在对金朝的态度上,却是最坚定的主战派,和秦桧这样的主和派泾渭分明,他是誓死也要恢复故土的,要重拾旧河山,立场十分坚定。所以,历史到底该对韩侂胄做一个怎样的评价呢?可能并非一个奸字或者权字能了。
主战?主和?还是主守?
在如何处理和金朝关系的问题上,詹体仁显然和韩侂胄有很大的分歧。
如果说秦桧是主和派,主张维持现状、苟安江南、外交妥协、削减军备、依附求和,连尊严都不要了的话,韩侂胄恰恰相反,是主战派,主张收复失地、灭金雪耻,通过提升军事实力,进行全面彻底的对抗,这其实是很受众多热血爱国人士推崇的。但韩侂胄的主张也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金宋多年的对峙、消耗,到得南宋时,国力已经大不如前,如果要主动北伐,以武力收复北宋失地,一雪“靖康之耻”,必须积极扩军备战、大肆增加赋税提高军费以支持战争进程,而这会极大地加重民间负担,可能带来一系列副作用。
詹体仁是看到了这一点的,所以,他和秦桧、韩侂胄都不同,是坚定的主守派。
在詹体仁看来,南宋当时的综合国力不足以灭金,这种情况下轻启战端,并不理智。所以,詹体仁的主张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防御优先,比如加强沿江防线,修缮城池、屯田练兵;二是反对冒进,比如韩侂胄“开禧北伐”前的草率备战,詹体仁就直接说出了他的担心和不同意见——韩侂胄就是因为开禧北伐失败才失势后被杀的;第三则是经济务实,詹体仁主张“练兵积粟”,注重财政的可持续性增长,反对因战争透支国力——是不是听着有点耳熟?这已经颇有些深挖洞广积粮的感觉了。
詹体仁在桂林的前任蔡戡也是主守派阵营的大将,两人观点大体一致。在韩侂胄一方看来,随着蒙古的崛起,当时金朝又陷入内乱,正是南宋北伐良机;但在主守派这边,却清醒地认识到当时南宋的短板,比如骑兵匮乏、财政脆弱,金朝虽然已现衰败趋势,但又不至于马上崩盘,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烂船也有三斤钉。毕竟蒙古刚刚崛起,有威胁,势却尚未大成,所以,还是需要采取守势,待时而动。
现在来看,应该说詹体仁和蔡戡们的观点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而且,他们与主和派靠签订不平等条约、换取短期和平不同,他们试图维持均势外交,主张充分利用金朝和蒙古之间的矛盾,避免完全依附某一方。然后,在承认南宋相对弱势这个现实的基础上,通过防御和内部改革来维持长期对峙,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保住南宋王朝尊严的前提下,等待金蒙矛盾激化和内部改革成功后出现的转机。
蔡戡和詹体仁的主守路线,本质是在南宋“战不胜,和不安”的困境中,寻求一条立足现实、兼顾尊严和生存的中间道路,看上去是更务实。不过,我们现在跳出圈外、隔着这么多年看问题,永远要简单得多,如果身处当时南宋复杂的国内和周边局势,问题可能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蔡戡是主守派的代表性人物,詹体仁也是,然而,他们有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注定了决定南宋命运的,不会是他们。
当然,作为长期在地方工作的蔡戡和詹体仁,务实亲民的作风,决定了他们对底层民生的悲苦耳濡目染后产生共情的概率,要比韩侂胄、秦桧们所处的地位大得多,所以,在他们执政桂林的那一段时期,对于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来说,怎么来看都应该是件好事。比如说蔡戡那一年,正是整个广西闹饥荒的时期,他开仓放粮,很是缓解了当时民众的困境。詹体仁也是一上任,就想方设法免除了桂林周边很多地方的赋税,尽力恢复经济,让民心振奋。但在南宋外忧内患的大环境下,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老雁一声霜满天
詹体仁字元善,建宁府浦城人(今福建南平浦城县),生于绍兴十三年(1143年)。他是隆兴元年(1163年)的进士,首次为官是在饶州浮梁(今江西景德镇)当县尉。《宋史》有专门的詹体仁传,这算是相当不错的了,很多可能名气比詹体仁更大的官员、学者都没这待遇。
有趣的是,在桂林老大的位置上,出现过两位姓詹都被叫做体仁的官员,前后隔了也就不到二十年时间。因为桂林本地史料缺失或是其它原因,很多桂林人都把这两个人做同一人看待,弄了些乌龙出来。现在我们知道,其实这两人一个生在浙江,一个来自福建,从年龄上看,也算两代人了。
前面的这个叫詹仪之,字体仁,之前我们就聊到过他,后面这个詹体仁,却字元善。有意思的是,这两个人都和理学大师朱熹有交集,而且相交匪浅。
詹仪之,淳熙十年(1183年)来桂林当老大,曾在桂林留下了不少摩崖石刻,这是后面的詹体仁所不及的,至少我们一直还未见到詹体仁留下的石刻痕迹。而且,詹仪之和朱熹的交往过程中,詹仪之的地位明显要高一些,而詹体仁实打实是朱熹的学生。
如前所述,1169年,詹仪之还赋闲在老家和乡邻吹水讲故事的时候,朱熹就亲自上门拜访过詹仪之,两人在关于理学的学术问题上,进行过深入细致的交流,均表示受益匪浅。三年后,詹仪之邀请朱熹来他老家的书院讲学,朱熹不问报酬,乐颠颠地来了。朱熹甚至还在詹仪之家门口的池塘边留下了一首诗,那“问渠那得清如许,为由源头活水来”的名句,竟被后人吟诵了近千年。这还不算,后来詹仪之来桂林当大官,状况不佳的朱熹还写了封求助信向詹老大诉苦,并且还有就盐政问题通风报信之嫌。由是也可看出在朱熹的心里,那确实是把詹仪之当兄长和朋友以及同学来看的。詹仪之故去后的第二年,朱熹专门到詹仪之下葬的地方悼念,还写了篇《祭詹侍郎文》的文章,感情也是相当真挚。
詹体仁不同,詹体仁实打实是朱熹的学生,“少从朱熹学,以存诚慎独为主”。他做人的原则是“尽心、平心而已,尽心则无愧,平心则无偏”。理想是好的,但现实总是那么残酷,尽心、平心,挺好的,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庆元党禁中,詹体仁因为有朱熹这层关系在,也被列入了黑名单,被罢官回家吹水去了。这不奇怪,以韩侂胄手下那班人的脾气,老师都被批判了,继承老师衣钵的詹体仁你能逃得过?
因为在绍熙内禅中跟着赵汝愚冲在第一线的原因,詹体仁这一赋闲就是八年,“屏居八年,知靖江”,几乎覆盖了整个庆元党禁的全过程,直到党禁运动偃旗息鼓后,嘉泰四年,也就是1204年,詹体仁才重新复出,接主守派同道蔡戡的班,知静江府兼广西经略使,当上了桂林的老大。
从时间点上来看,蔡戡辞职,身体是很大原因,但应该也有不太满意韩侂胄大张旗鼓准备北伐而不顾民生的想法。而詹体仁当值的这两年,正是韩侂胄把北伐事业干得如火如荼的当口。作为主守派的代表人物,身处西南边陲,詹体仁除了提出建议外,却也并不能左右大势,“侂胄建议开边,一时争谈兵以规进用。体仁移书庙堂,言兵不可轻动,宜遵养俟时。”虽然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比党禁时好了很多,但这个时候的詹体仁,有了前车之鉴,估计也是很无奈的感觉。所以,他能做的,也只是向上级申请“阁十县税钱一万四千,蠲杂赋八千”,减免一些当地的税赋而已。
在这期间,詹体仁曾预测过皇甫斌的败局,说“皇甫斌自以将家子,好言兵”,詹体仁私下跟同僚说,“斌必败,已而果然”。但他没有直接说韩侂胄必败,应该是吸取庆元党禁的教训了。这个皇甫斌也是和詹体仁一起上过党禁黑名单的,为三武将之一,遇到韩侂胄北伐,心里面应该是很激动的,不管不顾地准备大干一番,这可能也是后人把皇甫斌又归入到韩党阵营的原因吧。
詹体仁曾写过一首诗,名为《过广陵驿》:
秋风江上芙蓉老,阶下数株黄菊鲜。
落叶正飞扬子渡,行人又上广陵船。
寒砧万户月如水,老雁一声霜满天。
自笑栖迟淮海客,十年心事一灯前。
这首诗写于何时,至今已无考,不过,如果说是在表达詹体仁离开桂林后的复杂心情,倒也合适:韩侂胄不听劝,何尝不是取死之道?我也老了,没有办法做什么了。唉,世事就是这样,旧的去了,新的总会来,你看行人又上了广陵船。只能苦笑一声了啊……真是十年心事一灯前,孤独寂寞冷。
一年后,詹体仁卒,享年六十四。
来源: 桂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