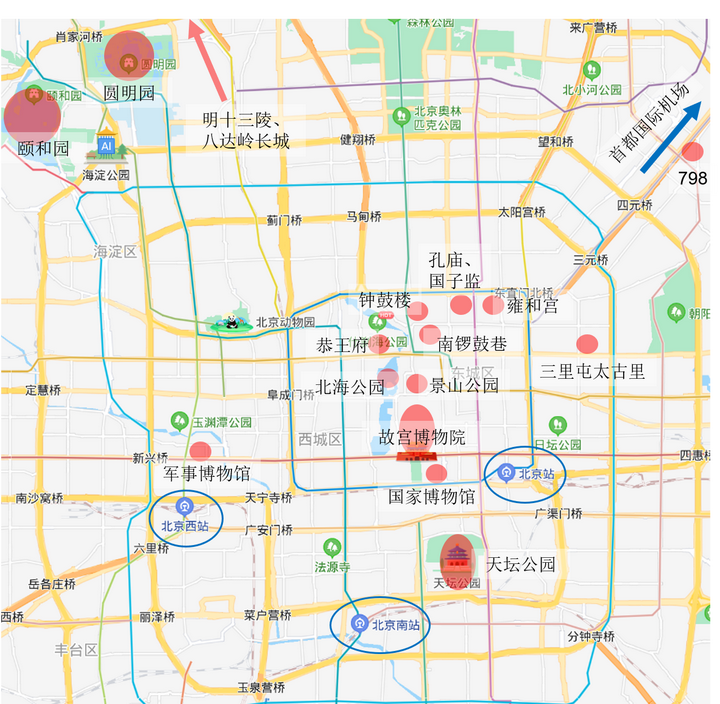为何藏传佛教那么恐怖(藏人独创的美学法则)
2024-09-15 08:01:25 家电

有朋友曾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藏区、祖国内地和日本都流布的是佛教大乘教派,为什么其佛教绘画差别那么大?为什么藏传佛教绘画中会有那么多千奇百怪恐怖的形象?”这还真得从藏传佛教的独特性说起。佛教的根本教义是“诸法无我”,宇宙万物无非都由“因缘所生”罢了。从此立场出发,佛教是彻底的无神论,当然这仅仅是指原生初始的佛教而言。佛祖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由于对其教义的不同理解,产生了不同的派别。其中大乘教派不单把佛陀神化,而且还制造了其它许多佛。
大乘引进了一种菩萨信仰,认为在宇宙中有许多菩萨存在,予人以幸福快乐。总而言之,自从大乘佛教兴起后,佛教遂变成了多佛、多菩萨以及多鬼神的“多神”崇拜。
藏区原是信仰自然崇拜的苯教。当佛教从印度、尼泊尔传入西藏时,一开始遭到了吐蕃社会权贵们的极力抵制反对。佛教为了在西藏扎根、生存、发展,采取了各种办法。其中最让人称道的是,从乌仗那迎请来的莲花生大师在印度密教的基础上吸收西藏本土苯教驱邪镇魔的许多仪轨,并将苯教的众多神灵降伏,吸纳为佛教的护法神,完成了佛教的本土化。从此,藏传佛教以新的面貌出现在藏人面前,受到藏族社会的欢迎。由此,藏传佛教所崇拜的万神殿自然便显得比内地和日本大乘佛教崇拜的更是复杂多端了。
那么,藏传佛教美术程式化形象造型就一种模式吗?不,问题不是一句简单的程式化就能说清楚的。我们在欣赏藏传佛教美术作品时,发现佛陀、菩萨、护法、乃至动植物、山石、建筑等许多物象造型,都是画师们善于认真观察物象,对物象由如实描写到删减不必要的细节,紧紧抓住对象的基本形态,进行概括、提炼、抽象而造型的。这是一种艺术家对事物本质认识的深化和把握过程。其结果,这类物象通常只以一些局部的改变而成为具有较稳定和固定形态的类型化形象。
它们一旦成型,便恒常不变。即使有所变化也非常缓慢,而且不会远离基本常形。这类程式化形象造型在藏传佛教绘画中比比皆是。如佛陀造像中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好”之标准;菩萨、诸女神的脸型为美丽的蛋卵形和芝麻形;而饿鬼、食肉恶魔的脸型为丑恶的方形和球形等均是突出基本常形的程式化样态。至于历代的高僧大德、吐蕃赞普、后妃、名臣、以及著名的历史人物的造型也都中规中矩,比例得当,勾勒匀整。只不过这类人物造型写实成分更多而已。
在藏族绘画、雕塑、金属造像中,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密宗造像,其形象在现实中难以寻觅,它们并非客观的实在物象,而是人们在头脑中虚构和臆想出来的理想化的物象。这类形象旨在表现某种特定的主观观念和理想,被赋予了某种特定的象征意义。藏传佛教教义认为,佛陀、菩萨皆有二轮身,一种是正法轮身,即真实身;另一种是教法轮身,受大日如来的教令,由大悲而转呈出威猛愤怒相,以此来降魔敌,醒愚顽。佛的教法轮身,因降伏魔鬼而无坚不摧,故称金刚;醒愚顽而使修行者、信众开悟,故叫明王。这些金刚、本尊、护法、明王因其神性而常见多面、多臂、多足;有的面孔常具三眼,并且身材粗短、壮实以示伟力。常见的还有牛头、马面等各种动物形象。这种虚幻、怖畏的造型,其目的就是为了寄托人们的一种理想,起到一种祈求镇伏邪恶,降伏观者心魔的作用。
在藏传佛教美术中,象征性无处不在,这是造型艺术的又一种表现形态。所谓象征形象,是指以最大的概括性和表现力表现某一种思想、某一现象的造型形象。实际上,在造型艺术中,象征造型往往只起到一种符号作用,它离不开特定的象征寓意。
藏传佛教美术中最具代表性的程式化象征性形象造型是曼陀罗。曼陀罗,梵文意为“坛”、“坛城”。印度密教在修法时,为防止魔众侵入,破坏修法,在修法地点划一圆圈,或修一土城,有时在上面画上佛、菩萨像。此修法处便称为曼陀罗。曼陀罗传入西藏后获得了很大发展。作为一种古老的象征符号,它的造型是程式化的。坛城的构图为圆形,外面三——四层,分别是护法火焰墙、金刚杵墙、八大寒林墙、莲花墙;和圆形相连接的是方形建筑,一般六层,用白、兰、黑、黄、红、绿六色表现护城河与建筑的装饰结构;再里是圆;在金刚墙包围之中居住着本尊和它的眷属。其它一切空白处布满花草、法器、吉祥物。
很显然,坛城就是用这种秩序严密和高度集中的几何图形构成基本的空间结构,表现其密宗理想世界的平面结构,从而被当作整个宇宙与人心的象征物。在藏传佛教美术中,我们还经常见到的“八吉祥徽”图案,也是一典型的程式化象征性图案。其右旋法螺象征佛音远播;吉祥结象征佛教教义在大千世界中贯穿始终;宝伞象征佛法能庇护万法;法轮象征法轮永转,佛法永布世间;胜利幢象征佛法之力量无敌不灭;宝瓶象征佛教宝藏无尽;双金鱼象征佛法能给众生自由与解脱;莲花象征佛教清净而不染尘俗。如此等等,不胜枚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