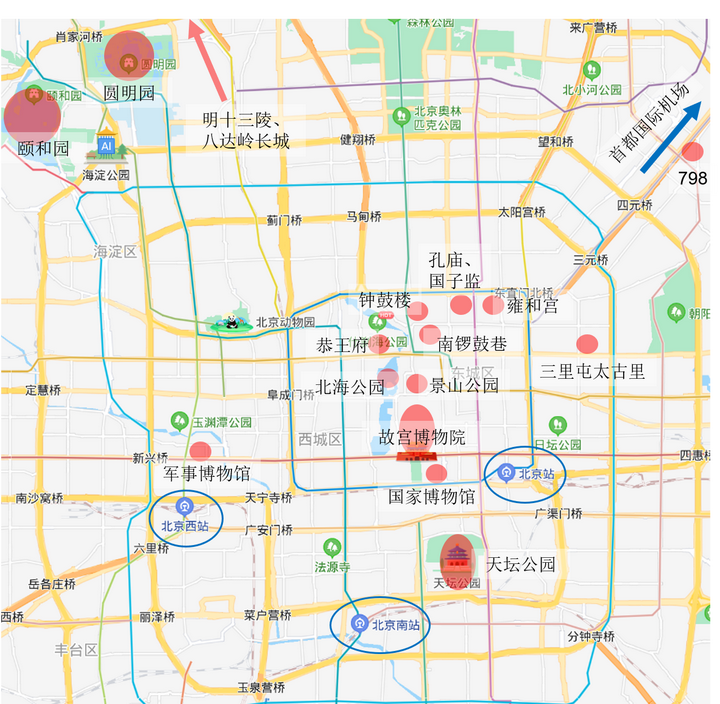明星科学家的成名之路:朱利安·赫胥黎
2025-02-27 13:38:00 实时讯息
朱利安·赫胥黎是科学家转型为科学作家和公众人物的典型例子。他是少数几个真正放弃学术生涯而投身写作和其他形式的社会活动的专业科学家之一。他也是少数几个雇用了文学经纪人的人之一——即使是多产的汤姆森也在自行管理与出版商的关系。赫胥黎出生于知识精英阶层,起初他利用的是T.H.赫胥黎的孙子这一名声。他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就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当时他的研究引发了关于延续青春的前景的头条新闻。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定期出现在杂志、日报和广播中。他曾与最著名的作家之一H.G.威尔斯在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重大教育项目上合作。他被普遍地认为是这个国家的顶尖知识分子,是“最好的头脑”之一。他对广泛的社会和智识议题有自己的看法,从支持包括优生学在内的精英立场转变为更加自由的立场。他成了人文主义哲学的积极倡导者。当他从动物学会秘书这一职位上退下来时,他在公共活动之外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职业,最终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负责人。尽管他参与了公共事务,但他的研究已经足以让他获得梦寐以求的皇家学会会员。当他从伦敦动物园辞职时,他已经被普遍地认为是新达尔文综合理论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然而,他现在被科学界斥为半吊子,这一观点似乎在他放弃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得到了证实。

朱利安·赫胥黎
赫胥黎早年就开始撰写关于科学及其影响的评论。他的《动物王国中的个体》是为《剑桥手册》系列写的,当时他只有24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他开始定期为《雅典娜神殿》、《双周》(Fortnightly)、《田野》和《乡村生活》等高质量杂志撰写文章。他的信件显示,到1921年,他已经通过伦敦的一家文学代理商将文章刊登在英国的杂志上了,并通过埃德温·斯洛森的科学服务社将文章刊登在了美国的媒体上。他在《世纪杂志》(Century Magazin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寻找长生不老药》(“The Search for the Elixir of Life”)的文章,赚了200美元。1924年,《旁观者》杂志以每千字4英镑的价格,刊登了7篇关于他在美国生活的文章。他的《生物学家随笔》(Essays of a Biologist)和《大众科学随笔》(Essays in Popular Science)收集了他更多的实质性文章,尽管这两本书的读者群有限。1924年,他为美国版的《生物学家随笔》获得了100美元的预付款,并在出版商克诺夫出版社(Knopf)所称的“令人失望”的437本的销量中获得了9.25美元的额外收入。
赫胥黎较为严肃的文章针对的是知识精英,很难“受欢迎”。但他对荷尔蒙的研究引起了公众的共鸣,因为它似乎证实了关于返老还童疗法这个耸人听闻的故事。1920年1月,他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给蝾螈喂食甲状腺提取物的影响的论文(蝾螈通常在成年后仍保留幼鳃),《每日邮报》以《生命的秘密》为题对此进行了报道。赫胥黎为该报撰写了一篇文章,以澄清这一情况。后来他声称,因此获得的10几尼使他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他有可能在大众科学写作的基础上开创一份事业。他为《每日邮报》撰写了一系列“科学笔记”,但很快就被告知他的材料太难了——《泰晤士报》也有同样的反应。然而,赫胥黎逐渐建立了作为一名日报撰稿科学家的声誉。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在《标准晚报》上已被读者所熟悉。他还为更通俗的杂志撰写文章,尽管斯洛森告诉他,一篇500字的报纸文章可以吸引数百万读者,而一份5000字的杂志文章只能吸引几千名读者。打入这个市场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赫胥黎必须学习适合每个出版层次的技巧。但同样明显的是,他决心以一种让自己有别于大多数科学家的方式做出努力。
随着在文学和新闻事业方面的不断发展,赫胥黎的活动变得更加务实。他扩大了活动范围,包括编辑工作和电台广播。他很早就愿意使用代理来发表杂志文章,这表明他比大多数在职科学家更认真地对待这方面的工作。到了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使用文学经纪人来处理所有事务,首先是历史悠久的詹姆斯·B.平克(James B. Pinker)公司,当该公司在20世纪末破产后又换成了A.D.彼得斯(A. D. Peters)公司。他们与编辑就文章的稿费进行了谈判——赫胥黎不愿意写更难的文章,除非值得他花时间去写。莱斯大学保留的他的通信以及他在A.D.彼得斯公司文献中的文件——现在保留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的哈里·兰塞姆中心(Harry Ransom Cente),证实了他是一位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一活动的商业方面的作家,并准备为此付出大量努力。他的代理人总是在寻找更好的报酬、再版和缩略本,以及国外的版权和翻译。
赫胥黎也越来越多地涉足出版业。他为《剑桥科学和文学手册》、本的《六便士图书馆》,以及后来的鹈鹕系列撰写了教育系列。他为汤姆森的《科学大纲》等文集做出了贡献,并最终接替汤姆森成为《家庭大学丛书》的科学编辑,每年获得75英镑的预付金。他是《大英百科全书》第14版的生命科学编辑,该书于1929年出版。1935年,他获得了250英镑的年薪,加入图书协会(Book Society)董事会,向会员推荐书籍,但几个月后他就辞职了,因为他太忙了。他举办讲座,包括在美国旅行期间。他听取了伯特兰·罗素关于报酬的建议。他制作了野生动物电影《甘尼特的私生活》(The Private Life of the Gannett),并定期出现在电台的广播中。
1927年,他决定辞去伦敦国王学院的教职,专心撰写《生命之科学》,这是他越来越多地参与大众科学写作的最明显的例子。这让他的同时代人感到震惊,《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社论,怀疑大众科学的市场现在是否真的大到足以维持该领域的专业作家。考虑到赫胥黎被视为全国薪水最高的教授,这一举动是大胆的。在莱斯大学短暂逗留期间,他的年薪相当于750英镑,而在国王学院,他的年薪为1000英镑。他并不依赖于从写作中赚钱,这表明他以作家的身份建立一个平行的职业生涯是源于对公众影响力和认可的真正渴望。现在,威尔斯在《生命之科学》方面取得的进展足以让他完全放弃自己的学术生涯。威尔斯是个严厉的监工,但他教会了赫胥黎成为一个职业作家所需的技巧。此时此刻,他是否能以一名独立的科学评论员开始自己全新的职业生涯还纯属猜测。事实上,他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继续工作,直到 1935 年成为动物学会的秘书。但他仍然想对英国的科学是如何进行的施加影响,正如达西·温特沃斯·汤姆森(D’Arcy Wentworth Thomson)在一系列信件中告诉他的那样,在专业科学界之外,这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汤姆森还怀疑赫胥黎能否无限期地承受自由职业记者的压力。
赫胥黎的通俗写作一直引起他的同行科学家们的关注。他回忆说,当他的作品第一次出现在日报中时,他被霍尔丹和其他人警告说,这可能会损害他的职业生涯。这些担忧在赫胥黎有望入选著名的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后的几年成为现实。当选会员是基于他作为一名研究人员的地位而考虑,但在他的同龄人中有一种感觉,现在他被职业生涯的另一面(即大众科学写作)分散了注意力。赫胥黎在1926年和1927年再次考虑参加选举,十年后也会处于同样境况的霍格本担忧,赫胥黎决定辞掉国王学院职位可能会对他不利。事实上,他没有当选,当1931年和1932年他再次参加选举时,人们也表示了担忧。反对意见并不完全集中在赫胥黎的写作活动上:遗传学家F.A.E.克鲁承认谈论生物学和人类事务是不受欢迎的,但也指出,皇家学会的动物学部门由不喜欢实验工作的老式生物学家主导。赫胥黎本人注意到了对传统话题的偏爱,同时抱怨说,既然他经常被要求为了官方科学机构的利益而运用同样的技能,那么对他的新闻活动进行批评就是不公平的。1932年,赫胥黎被排除在候选名单之外,D.M.S.沃森告诉他,委员会的几名成员希望看到他的学术作品,以确保他仍然是一名“活跃的动物学家”。
这些评论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表明一位科学家在其职业生涯中确实因其在大众科学领域的活动而遭受到了痛苦。其他科学家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特别是霍尔丹和霍格本,但这一案例提供的不仅仅是谣言和猜测。然而,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赫胥黎发现很难从年长的动物学家那里获得支持还有其他原因,即这些动物学家对遗传学和实验工作持怀疑态度,他们主导着皇家学会的这一部门。其次,赫胥黎本人抱怨对他的“新闻”活动缺乏欣赏,这被认为与人们可能会为高雅的杂志或自我教育市场而开展的严肃的非专业写作非常不同。许多科学家从事后一种活动,因此他们不太可能不赞成赫胥黎通俗作品的这一部分。问题是,他在报纸和广播上发表了具有争议的观点,这更有可能引起反对,尤其是当他看起来像是为了文学事业而放弃研究的时候。如果他真的放弃了研究,他就不太可能进入皇家学会,人们不能责怪委员会的那些人想要确保情况不是这样。最后,赫胥黎确实成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那是在他接受了伦敦动物园的工作而重新加入了专业团体之后。
克鲁发现的另一个问题是,赫胥黎对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评论的意愿。他是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的活跃成员,并提倡人文主义哲学,把这作为传统宗教的替代品。他1927年的《没有启示的宗教》和1931年的《我敢怎么想?》(What Dare I Think?)被广泛讨论,这两本书比大多数曲高和寡的书卖得都好——《我敢怎么想?》在三个月内卖出了3300本。赫胥黎也在更受欢迎的层面上写了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1939年,理性主义者出版协会以2d(d表示旧的便士)的价格发行了一本他的小册子,名为《生命是值得的》(Life Can Be Worth Living)。对于科学界的保守派成员来说,更令人不安的是,赫胥黎正成为纳粹及其英国支持者(包括E.W.麦克布赖德,他在动物学会的主要反对者之一)所宣扬的种族主义生物学的高调的评论家。他与人类学家A.C.哈顿合著的《我们欧洲人》一书,有力地说明了新的群体遗传学正在削弱关于不同种族类型的旧理论的科学可信度。
到20世纪30年代末,赫胥黎致力于在动物学会的要求与他的雄心之间取得平衡,他的雄心是就科学进行写作,以及对现代世界的问题进行更广泛的写作。我们可以从他的第二个文学代理人A.D.彼得斯的档案中了解他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以来的写作活动。从提交给赫胥黎的记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从事的一系列活动的复杂性。准备中的新书源源不断,他通常会先收到100英镑预付款。像往常一样,当销售额超过最初的预付款时,就会产生版税。文章、缩略本、翻译和电台广播都有单独收费。许多报酬微不足道,通常只有几英镑或几几尼,但偶尔也会有更可观的报酬,比如他在《每日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篇1200字的文章,得到了30几尼。稿费很多,每年加起来就有数百英镑——这给他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1942年,他辞去了在伦敦动物园的工作,这一年他总共赚了接近250英镑。这一数额直到1945年才大幅增加,当年的总额跃升至接近9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也显示了赫胥黎是如何通过提高他的作品量来弥补他的薪水损失的。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公众人物。然而,就大多数科学家而言,他把自己边缘化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渴望已久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已经被他收入囊中了,然后又被浪费了。
(本文选摘自《主动出击: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英]彼得·J.鲍勒著,王大鹏、周亚楠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英]彼得·J.鲍勒/文,王大鹏、周亚楠/译